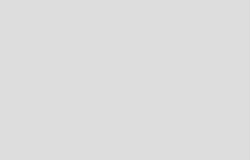反绑双手的惨死者 | 罪案遗踪

►图片来源:Pixabay
“罪案遗踪”系列 第2篇
《知识分子》科学新闻实验室 第5篇
撰文 | 格蕾丝(《知识分子》科学新闻实验室特邀作者)
翻译 | 张 晗
责编 | 黄永明
● ● ●
2014年2月,我爬进一座位于危地马拉乡下的高海拔山坡上的万人塚,协助发掘和记录里面的遗体。这座坟墓是危地马拉持续了36年的内战所留下的一个痕迹,那场战争随着1996年和平协议的签订而结束。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1]的法医人类学家们发现了这座坟墓,然后为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法医人类学田野实训学生建立了开挖基坑。
墓穴是一个狭小的深坑,勉强能让我和已经在里面的另外两个学生容身。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两处墓穴,我们会轮流进入。一名学生需要困窘地把身体紧贴在坑壁上,才足以让我走到分给我发掘的遗体旁边。有人从上方把工具递给我:一把刷子,一个用来筛土寻找细小碎骨的滤器,和一个簸箕。我蹲伏着保持平衡,一只脚放在身下,另一只脚由于空间的限制只能不牢靠地踩在坑壁上。调整身体重心时,我甚至都没法避免更多尘土滑落到我正在尝试清理的区域。
与此同时,来自附近村子的人三五成群地站在地面上,用当地的曼姆玛雅语交谈着,我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有时候某个人会从基坑边缘窥视我们,有时候我能捕捉到西班牙语的只言片语,我注意听的话能听懂个大概。孩子和狗也在我们头顶上跑来跑去。一个小女孩的一只小小的塑料鞋滚进坑里,落在我们身上。另外两名学生中的一人把鞋子递给了上面的人。到那一周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掉下来。
然而,有种糟糕的感觉我从头到尾都没能习惯——哪怕仅仅失去平衡一秒钟,我都有可能不小心向前滑跌到其中的一具骨骸身上,毁坏一项战争罪的宝贵证据。
宋慈是对的
在美国这边,谈起法医人类学,几个著名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现代法医人类学的讨论中,其中有威廉·巴斯[2]和克莱德·斯诺[3]。斯诺曾在阿根廷和危地马拉帮助训练法医人类学家。
不过法医人类学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法医人类学和法医病理学可以被看作我们英语中所说的“一枚硬币的两面”[4];更确实地说,是一具遗体的两部分。法医人类学研究骨骼,而法医病理学关注软组织。已知最早的法医病理学著作《洗冤集录》出版于1247年,作者宋慈是南宋的一名验尸官。
宋慈把有些事情搞错了。比如他说人体有365块骨头,但实际上科学家一致认为一名成年人体内骨头的数量是206块。即便是在从出生到童年的这段时期,我们的许多骨头仍处在融合的过程中,但总数也从未超过270。知识小课堂:即便在你停止“长身体”(长高)——一般是14到16岁之间——之后, 你体内的某些骨头仍在生长(融合到一起)。两段锁骨在胸前的连接处通常是最后融合的,可以晚至你30岁出头才发生。
宋慈在其他一些事情上是对的,考虑到他那个年代在技术资源和生物学理解上的局限性,这是令人叹服的。在《洗冤集录》1980年版英文译本序言里,李约瑟和鲁桂珍指出宋慈识别出了数个“人体表面受到创伤后尤其可能危及生命的位置”。这些位置已经得到了现代法医学的承认,“它们在今天的重要性相较于宋慈的时代也丝毫不减”。
《洗冤集录》还有一章是关于检验死亡很久后的骨头的,这部分现在主要是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
尸体农场
[提示:后续几段话中关于人体腐烂过程的描述可能引起不适。]
并不是所有法医人类学家都同意“组织—骨骼”是他们与法医病理学家之间最好的分工方式。“最好是在情境中观察骨头,看到周边组织的关联情况,以及组织是否有创伤的迹象,”密西西比州法医办公室的全职法医人类学家斯蒂芬·赛姆斯[5]博士说。“我最初的几份工作是和法医病理学家一起尸检,但我知道有些地方甚至都不让法医人类学家参与尸体解剖。”
赛姆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法医人类学创伤分析”。他从1979年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时他还是美国第一所露天法医人类学研究机构——也就是“尸体农场”——的助教,这一机构由威廉·巴斯博士建立于田纳西大学,直至今天还在运转。这些年来,其他的尸体农场在我的国家美国各处开设起来,两座在德克萨斯州,一座小型的在东海岸,一座在中西部,一座在西部。当前,美国共有六处露天人体腐化研究机构。
尸体农场的建立,是为了让科学家研究生物体——尤其是人体——在死亡后是如何分解的。那里的研究使得科学家可以记录到许多细节,像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尸体分解的速度有多快;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化学物质如何影响尸体腐化;掩埋的操作会如何影响尸体腐化;哪些昆虫会寄居在尸体上,以及它们出现的时间表;焚烧和冷冻有机组织会如何影响腐化;诸如此类。
尽管我在2011年访问了田纳西大学,我却从未去过尸体农场。它对公众是不开放的,许多此类研究机构都是如此。游客污染研究结果的可能性实在太高了。但是我可以根据我掌握的知识想象那个场景:一万平方米的草地和林地区域里,躺着大约150具尸体,有的在地上,有的埋在土里。尸体农场刚刚出现的时候,当地人曾抱怨说他们能够看到那些未被掩埋的正在腐烂的尸体,后来高高的用于遮挡的篱笆就被建立起来。
尸体可能随着脂肪和肌肉的分解而变干,或者它们先是肿胀,然后皮肤随着细胞死亡的发生而分裂。阳光照射之下,皮肤颜色变深,就像是晒成棕褐色的皮革,紧紧地绷在骨头上,直到它也消失掉。附近的昆虫以特定的时间表来到这里进食尸体。较为大型的食腐动物可能会把肉从骨头上咀嚼下来,在骨头上留下牙印。2017年5月,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法医人类学研究所(也就是“尸体农场”),一只鹿正在咬人骨。尽管科学家知道鹿偶尔会吃肉,但它们是被当做食草动物的。2017年5月的这张照片,是鹿吃人类腐肉尸骨的首个影像证据。
尽管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自2014年就开设了尸体农场,但是人体遗骸的使用在澳洲饱受争议,而在英国则是违法的。可是我们美国有六座尸体农场。六座!都在一个国家!我不禁想,相较于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对于死亡有着某种痴迷。或许是对于收集荒诞数量的科学数据有什么执念。也许两者都有。
当我告诉赛姆斯六座尸体农场在我看来似乎太多的时候,他笑了。“我们可以在每个州的各个角落开设一个,收集新的数据。”他说。他说的是事实:尸体腐化因气候而异。不仅不同地区的气候各异,同一地区的气候也由于海拔高度、城市发展等诸多原因而多种多样。
成千上万的细节
我第一次见到海瑟·沃尔什-哈尼[6]博士,是2014年2月法医人类学田野实训期间,在危地马拉城的维尔维娜公墓。沃尔什-哈尼是佛罗里达海湾海岸大学的副教授,同时为好几个佛罗里达法医区担任法医人类学顾问,她在田野实训里手把手教学生如何做骨骼鉴定和评估。
维尔维娜是危地马拉城的一座主要墓地,内有单独的万人塚,即藏骨堂。维尔维娜的空间极其有限,家属要为埋葬亲人的地下墓室支付租金。(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是常见,反正在美国不是。我们美国人一般是在公墓买一块地,或者火葬后将骨灰交还家属。)如果太多次欠缴租金,家人的遗骨就会被丢弃到藏骨堂里。
很多人认为在危地马拉内战期间,警察杀害的人的遗骨被暗中送入了维尔维娜的藏骨堂。因此,2010年,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开始了发掘其中遗骨和建档记录的工作。
作为学生,我们的工作是记录与评估藏骨堂里那些已被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的专业法医人类学家记录和分析过的骨骼。在基金会设在维尔维娜公墓的临时帐篷里,我小心翼翼地开始把“我的”研究对象按照解剖学的正确位置摆放在桌上。当我看到高大却并不起眼、性格开朗而富有耐心的中年女人沃尔什-哈尼博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指导学生,我有点恐慌。我实在很想弄好我分到的骨骼让她检查,但是有几块肋骨丢失了,我也很难找出其他肋骨的正确顺序。
作为参考,人体有24块肋骨,左右两边各12块。我修过两次人体骨骼分析的课程,本科生时一次,研究生时又一次。为了把几百块骨头摆放到正确的位置,需要记住成千上万的细节。如果有骨头破碎和/或遗失,那就更复杂得多了。
在把肋骨从所有骨头里捡出来之后,我把它们分成了三堆:左侧肋骨、右侧肋骨和我无法辨认的碎片。在学校里我们拿到的是完美的样本,但现实中,在秘密地点、万人塚和类似环境里找到的遗体,骨头是断裂、破碎的,有时被焚烧过,有时整个缺失。
最上端的两对(第1、2肋)和最下端的两对肋骨(第11、12肋)在形态上和其他肋骨存在显著的不同,意味着找到它们的位置相当容易。我正和剩下的8对肋骨较劲的时候,沃尔什-哈尼走过来帮我。
在我完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期间,我们也查看了颅骨。在前面一周的实训课程里,我们跟着基金会的法医人类学家学习了鉴别各式各样武器造成的颅骨骨折模式,不过我没能在这个颅骨上发现任何明显的骨折。沃尔什-哈尼把头骨的转过来,指着前臼齿上的一个明显的凹陷。“看到了这个吗?”她说。“这应该是头的侧面被钝器打击造成的。”
我从她手中拿过头骨,仔细检查那颗受损的牙齿。它甚至都没有松动。它让我想到扁平而黯淡的珍珠。
我长出了口气,都没发现我一直在屏住呼吸。不论我学习多少人体骨骼分析知识,都是远远不够的。
死亡到发现之间
法医病理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确定死亡时间[7];埋葬学,研究在机体死亡到遗体被发现之间都发生了什么。尽管赛姆斯和沃尔什-哈尼专攻的都是创伤分析,但赛姆斯说,“创伤和埋葬学是紧密相连的。”
“埋葬学有无穷无尽的变量,”他继续说道,“它比我们做的大多数事都要复杂。它难以重复,难以复现,难以模拟。创伤也一样。创伤很难伪造,很难在人体以外的物体上呈现,也很难量化或者检验。”
确定死亡时间在危地马拉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山坡上的坟墓埋葬的是军营里的平民囚犯,他们在内战期间被安置在此处。信息源自当地村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亲属在几十年前被从家中掳走,再也没回来。
然而在大多数发现身份不明人员遗体的案例里,正如赛姆斯和沃尔什-哈尼最可能在他们美国的日常工作里遇到的那样,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未知的,除此之外很多也是未知的: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机理;死者的年龄、性别、血统、身高。尸体农场收集到的数据就是用来帮助确定死亡时间的。
尽管其他的大学和组织也尝试了,但在田纳西之外的州开设露天尸体腐化研究机构却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经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4年在威斯康星的福克斯谷技术学院建设一座“寒冷天气下”的尸体农场的计划至今没有结果。
“很多州都有法律规定对死后的人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威斯康星,我们州的法律规定,尸体只能捐给医学教学机构,用作学生教具或者外科手术研究。因此我们需要修改州法才能开展人类学研究。” 福克斯谷技术学院法证科学系主任约瑟夫·勒费弗[8]博士解释说。
沃尔什-哈尼也曾尝试在佛罗里达建一所相似的机构,可是资金短缺和当地社区的反对成为了障碍。佛罗里达另一处研究机构于2017年5月破土动工,但研究工作可能直到2018年1月才能开始。(里面的尸体需要时间来腐化分解。)在如今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收集数据十分必要。
“我刚进入这一领域的时候,遗体变成白骨,部分组织留有脂肪但是基本上白骨化,大概需要7到10天,” 沃尔什-哈尼回忆。“自从这里(佛罗里达)的天气变得更加炎热干燥,这影响到昆虫密度,我见过遗体在4天之内就达到了同样的腐败程度。过去至少需要7天的过程现在4天就能发生,有时只要3天。”她认为这些变化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回到墓地
让我们一起回到2014年2月,回到危地马拉乡间山坡上的那座万人塚。是的,我很害怕我疲惫的双腿会坚持不住,让我跌倒在我一直协助发掘的遗体上。但我能感觉到的远不止这个。我希望你们明白,从万人塚里发掘遗体的时候,你从不会仅仅只有一种感受。如果你对法医人类学非常感兴趣,还有过人体骨骼分析的基础训练——即便我是个作家也两者兼而有之——你会感到毋庸置疑的兴奋,尤其是当你找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找到手部所有细小的骨头。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真实条件下我不该指望能找到所有的小骨头。但是,它们就在我眼前。
接着,我们在手骨旁边找到了一小段打着结的绳子,由此推测这个人的双手很可能被绑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拼凑起这个人死亡的过程。我愈发激动了!在大学的人类体格学实验室里花费的那些时间——熟记每块骨头的学名和形态学特征,学习利用形态鉴别骨骼碎片,练习根据骨长度和骨缝估计身高年龄——引导我走到这一步。
接着就是残酷而丑陋的顿悟:这个人死的时候双手被绑在背后。
此时我为我的兴奋感到羞愧。没有谁应该在发现这种事情的时候还感到激动。
我们把山坡墓穴里的所有骨骼打包之后,它们被送往位于危地马拉城的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总部等待鉴定。我则返回了美国。
有些时候,当我回想起危地马拉的那些坟墓,我仍然有种会失去平衡跌落到某人遗骨上的感觉。
关于作者
格蕾丝是美国的自由职业科普作者。她在匹兹堡大学主修写作和人类学,后来获得写作硕士学位。格蕾丝和她先生现在住在美国西北部。他们有三只猫,一只鹦鹉。
注释:
[1] Guatemalan Forensic Anthropology Foundation 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
[2] William Bass 威廉·巴斯
[3] Clyde Snow 克莱德·斯诺
[4]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一枚硬币的两面
[5] Steven Symes 斯蒂芬·赛姆斯
[6] Heather Walsh-Haney 海瑟·沃尔什-哈尼
[7] post-mortem interval 死亡时间
[8] Joseph LeFevre 约瑟夫·勒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