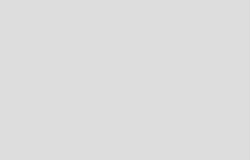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青蒿素类药物走向世界为何曾失败|科学春秋
爱迪生可能是当今世界发明创造最多的人,但却为何难称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发明不多,但为何他成为了人们眼中公认的科学家?
● ● ●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青蒿素类药物走向世界为何曾失败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科学家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研制青蒿素类药物的曲折历史。中国科学家从药用植物中发现青蒿素并对其进行结构改造后,将各种高效、速效的青蒿素衍生物向国际公开,寻求国际合作以造福更多疟疾患者。
这项国际合作没有能够成功,其中有科技体制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中国自身产业化能力的缺失以及对某些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分析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为以后中国药物研发之路提供一些借鉴。

►1981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署赞助的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SWG/CHEMAL)第四次会议。沈家祥(前排左一),周克鼎(前排左三),陈海峰(前排右四),曾美怡(二排左三),屠呦呦(二排左四),李国桥(四排左三),施凛荣(四排左四)。
撰文|黎润红 饶 毅 张大庆
责编|程 莉
1967年,中国为了支援越南抗击美国,最高领导下达了研究抗疟新药紧急援外任务(五二三任务)。在这项任务中,科学家从传统中药中发掘出了青蒿素,后来又相继研制出了3个疗效更好的青蒿素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双氢青蒿素)。为了提高治愈率和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医药学家们又在青蒿素衍生物的基础上,结合五二三任务中发明的其他化学抗疟新药,如本芴醇和磷酸萘酚喹等,研制出了各类青蒿素类复方药物,并通过国际合作,将青蒿素类抗疟药物推向世界([1],页1—23)。关于青蒿素以及青蒿素类药物的发现历程,笔者已有文章和书籍介绍[2—5],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如何寻求青蒿素类单方药物与国际的合作,国外的相关机构又如何来对待中方这个自主研发、疗效显著的抗疟新药。虽然说是合作,实则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有着多少曲折的故事,同时又有着多少无形的较量。虽然这是一段未能成功的合作,但是却也为后来复方药物的合作成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1、WHO对青蒿素类药物的关注
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创始国之一,从194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创议、筹备到1948年的正式成立,中国都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内政治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并未取得合法席位,直到1972年5月,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合法席位。同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戈林诺·戈梅斯·坎道(Marcolino Gomes Candau)访华探讨双方合作事宜[6]。1973年5月,卫生部部长黄树则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中国当选为执委会成员国。同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坎道宣布,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科教授张炜逊为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7]。1978年9月29日—10月15日,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Dr. Halfdan T. Mahler)访华期间,卫生部部长江一真与其就扩大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技术合作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技术合作备忘录》[8]。
随后,卫生部拟定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寄生虫病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会谈方案。该方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在中国建立世界卫生组织寄生虫病合作中心,包括血吸虫、疟疾、丝虫病等,另一个是合同性技术服务协定项目,主要是青蒿素类药物的研发、疟疾免疫等。
中方最初试图就青蒿素类药物与WHO开展多方位的合作,包括实施规划项目和建立技术合作方案、提供奖学金进行专业人才培养、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临时顾问、资助国内开展活动费用、购买仪器设备、短期访问和技术考察等。
198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培训研究特别规划署(The Special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TDR)/ 抗疟药物指导委员会(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Drugs for Malaria,CHEMAL)的彼得斯(Wallace Peters)教授应中国卫生部的邀请来访 ,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泽琳负责接待。会谈中,彼得斯教授建议以TDR / CHEMAL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并提出可资助中国学者到他的实验室做青蒿素的进一步研究。
1980年10月,李泽琳受WHO资助前往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LSHTM)彼得斯教授实验室开展青蒿素的药理研究工作。她是青蒿素项目最早派到国外做研究的学者。李泽琳原计划在英国工作一年,后因研究需要又延续了一段,于1982年1月回国。
李泽琳在出国前就已经开展了青蒿素类药物对疟原虫作用机理的研究,在国外则主要的研究工作包括:
⑴青蒿素类药物抗疟效果及毒性研究,用N株鼠疟原虫,对小鼠进行四天治疗实验及毒性试验比较,结果证明青蒿素抗疟作用好、毒性低而对氯喹抗性株数疟原虫实验表明对重度氯喹抗性株有一定交叉抗性。
⑵青蒿素及衍生物对鼠疟原虫糖代谢的影响。
⑶ 用同位素氚标记核酸前提次黄嘌呤渗入实验方法,研究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人体恶性疟核酸代谢的影响。几年之后在TDR的资助下上海药物所的顾浩明研究员也参加了这个团队的工作。
根据彼得斯教授的建议,并在WHO助理总干事陈文杰教授的积极推动下,1980年12月5日,WHO总干事马勒(H. Mahler)博士致信卫生部长钱信忠:“因为发展新抗疟药物非常紧迫,TDR / SWG-CHEMAL认为下一次科学工作会议应讨论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优先考虑在中国召开,并建议此会议于1981年4月上旬在北京或其他地方举行。” 根据马勒的建议,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交了申请关于在北京召开青蒿素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该报告于1981年4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由于“523办公室”已于1981年3月正式撤销,卫生部为此会议临时组建了会议筹备组。从当年4月下旬开始,会议筹备组参照WHO的提议,组织相关人员撰写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化学、药理毒理、临床研究等14篇报告并于6月下旬召开了审稿会,最终在14篇报告的基础上讨论汇总为七个方面的综合性报告,并组织人员进行了试讲和讨论。在会上,根据专家的意见,筹备组组织人员进行论文修改和补做一批必要的实验,草拟了与WHO合作的技术方案等 。同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主持成立了筹备领导小组。
2. 第一次达成协议
1981年10月6—10日,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培训专项资助的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SWG / CHEMAL)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为“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一次在日内瓦总部以外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中方宣读了7篇研究报告,主要内容为:青蒿素的分离和结构测定、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化学和化学研究、抗疟效价和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药物代谢及药代动力学研究、急性亚急性及特殊毒性试验报告和临床适用报告等[9]。在分组讨论时,国外专家就相关专题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双方同意按照会议报告中的内容进行合作,在化疗科学工作组规划范围内制订有关研究计划,以便使这些药物最终能应用于将来的疟疾控制规划 。
1981年10月12日,中方与WHO疟疾化疗组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中国青蒿素研究现状、合作研究、药物生产、成立指导委员会、学术交流、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相关内容保密、法律等相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
从会议相关文件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国际科研合作的规则还十分陌生,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只能依靠WHO相关部门。在科研合作中也存在着矛盾的心态,既想要快速了解国际规则又害怕合作给中国的科研成果带来损失,处处谨小慎微。不过,通过此次会议,中国科学家及科研管理人员开始了解有关药物注册、专利、研究工作的标准化等相关事宜。
依据1981年10月会谈的精神,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于1982年1月5—8日在北京召开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攻关协作会议。会议制订了1982—1983年的研究攻关计划,确定了两年研究的目标与重点为“按照国际新药注册标准要求,优先完成青蒿酯钠水注射剂、蒿甲醚油注射剂和青蒿素口服制剂的临床前药理毒理实验资料,为进一步实现三药商品化和国际注册确立基础”;同时,还提出了成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等,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制定和协调科研计划。另外会议还特别强调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科研成果是集体的成果:
1. 关于统一归口问题: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有关协作的日常工作由中医研究院牵头负责,遇有重大问题必须报请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审批。它的一切科研成果都是全国多部门、多单位长期共同努力协作的结果。为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在今后工作中,凡需向WHO或国外提供有关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资料、原料、制剂及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谈判等,均由卫生部外事局统一归口,根据情况由卫生部外事局与有关部门或单位协商处理,或报请上级批准。
2. 要继续发扬全国一盘棋和大协作的精神。会议认为要搞好与WHO的技术合作,首先是搞好我们国内的协作。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为我国首创药物,但要真正把这些新药达到国际注册标准,进入国际市场推广应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所能办得到的,必须依靠全国大协作和各部门、各单位共同支持,提倡全国一盘棋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攻关。

►1981年钱信忠与参会的国内外专家交谈
参会的有中医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及广东、广西、云南、山东等有关科研、院校药厂的代表共50多人。在这次会上,成立了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正式文件于当年3月20日下发 。
据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张逵回忆: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秘书处当时设在在中医研究院宾馆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只有两套办公桌椅、一部电话、一张双层单人床和几个资料柜,外地的秘书朱海同志来京办事也住在这里。周克鼎家住丰台干休所,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要乘公交车两个多小时到东直门这间办公室里上班,他放弃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可能升迁和提高待遇的机会,只为使青蒿素类药物早日走向世界([10],页48)。
1.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规划和与TDR拟定的七项合作
为了推动青蒿素类药物走向世界,1982年1月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攻关协作会议上提出了与WHO合作的建议,同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滕翕和起草了与WHO合作内容的清单。根据1981年10月会谈的精神,WHO化疗科学工作组将指派一名熟悉药物研究和药政管理条例的顾问访华,帮助中国推进研究规划和各项研究的标准化,最迟在1982年2月访问中国,为期2—3周。
1982年2月1日至14日,由TDR / CHEMAL指导委员会秘书特里格博士陪同药物政策顾问海佛尔(M. H. Heiffer)博士(美国华尔特里德军事医学研究所药物科主任),毒理学专家李振钧(Cheng Chun Lee)博士(美国有害物质环境保护办事处顾问)访华,参观了北京、上海、广州有关科研单位和桂林第二制药厂,组织了多次学术报告讨论,最后就两年合作研究项目与资助等问题双方交换了意见,同意从中方提出的合作计划中选出的七个课题上报CHEMAL(见表1),并就预期在两年内的合作事宜达成了共识。
 ►表1.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提出的7个合作研究项目
►表1.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提出的7个合作研究项目
WHO同意为中方提供培训计划(5名人员出国学习,包括药代动力学、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生物利用度测定方法、新药开发考察、临床药理学、毒理学五个方面),在中国举办气象色谱——质谱研究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药代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培训班,出国考察新药制剂研究与质量标准,以及到国外进行青蒿酯钠临床试用等初步达成了共识。拟同意在进行青蒿素衍生物临床Ⅰ、Ⅱ期临床试验期间,WHO派一名观察员来华指导工作,观察员为临床药理学家,主要实地了解临床试验情况 。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结合当时国内外实际情况,坚持两条腿走路,对未列入TDR合作计划而又需要研究的课题,如青蒿素口服制剂、抗疟作用原理、部分系统药理、延缓抗性产生以及资源调查等,将它们均列入国内研究计划(见表2)。
 ►表2. 1982年国内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抗疟药开发研究项目表
►表2. 1982年国内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抗疟药开发研究项目表
1982年3月1—3日WHO的SWG-CHEMAL指导委员会举行会议,3月26日特里格博士致函卫生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薛公焯:
SWG-CHEMAL指导委员会确认开发青蒿酯钠作为治疗脑型疟及其他复杂类型的恶性疟的可能性药物优先开发,并以青蒿酯钠制剂符合GMP 生产标准,该药的实验室和动物的设备情况符合GLP等为前提,同时提出Ⅲ临床观察与泰国进行协作时要使用符合GMP标准的青蒿酯钠进行,并且临床观察工作要全盘为泰国工作者掌握,然后对资助前往国外学习的科研人员偏向于与青蒿酯钠有关的人员。此外,还对药代动力学及代谢研究的培训班、新药配制的培训以及Beagle狗种的引进等提出了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
1982年TDR / CHEMAL制订的第一份“青蒿酯钠开发计划概要”,其目的是使用于治疗脑型疟,效果优于奎宁的高效低毒新药及其静脉注射剂型获得国际注册,具体目标是青蒿酯钠的开发工作在可进行临床研究的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因为中国的有些条件尚不完善,可由FDA的官员或官方的设计对已经做出的实验结果或者将要进行试验的地方进行检查,如果必须做而在中国不易开展的可在美国开展。比如:同位素标记物的开发研究、药代动力学研究等,还准备在美国开展Ⅰ期临床药理的研究等 。
1982年6月19日陈海峰、王佩代表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给特里格回信,告知中方对他3月26日来信的一些看法,提出如果时间合适,可以邀请他7月20号左右来华。中方与特里格大部分意见能达成一致,但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对Ⅲ期临床试验的看法希望能在7月份特里格等来华时再商议 。6月29日,特里格回信陈海峰告知,他在6月与TDR的坎菲尔,海佛尔,韦恩斯德费尔共同前往华盛顿与FDA商议派药品检验官员到中国的事宜,确定了9月来中国检查的人员和行程安排,并将安排告知中方 。7月,特里格又给陈海峰来了两封信,其中提到有不少科研人员向他们询问能否提供一些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样品供实验所用。中方于8月28日回信特里格,希望他们来后增加对昆明制药厂蒿甲醚注射剂的检查,提出增加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出访国外学习事宜,至于提供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样品事宜等则建议他们来了之后商量 。由于TDR和FDA人员只能在9月份以后才能安排时间来中国,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利用这一期间组织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桂林第一、第二制药厂、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对现有青蒿酯钠制剂,从原料制备、工艺流程、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评价和研究改进。因蒿甲醚的研发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因此增加了对昆明制药厂蒿甲醚注射剂的检查。
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于1982年7月10—19日在北京召开青蒿素衍生物制剂评议讨论会,重点评议了青蒿酯钠制剂的生产工艺。本次会议“确认使用碳酸氢钠溶液和改进的冻干制剂两种生产工艺作为下一步重点研究的剂型”。会议还认为,青蒿酯钠当前研究的关键是制剂的标准化问题,又在于严格按照GMP的要求抓好生产工艺和技术操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为了迎接GMP审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专门拨出经费,完善青蒿酯钠采用碳酸氢钠溶液和冻干制剂的生产工艺。同时对桂林第二制药厂青蒿酯钠制剂车间和昆明制药厂的蒿甲醚制剂车间进行了部分改造,增加设备,上海医工院派人培训,建立和健全有关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
1982年9月14日—10月2日美国FDA国际调查部调查员特兹拉夫(D. D. Tetzlaff),在TDR / CHEMAL的秘书特里格和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秘书周克鼎、李泽琳的陪同下访问了昆明制药厂、桂林第一、二制药厂。由于时间关系,特兹拉夫对昆明制药厂生产程序未能进行全面检查,但是通过工厂制定的管理规程和生产程序的质量控制等方面要求的文件检查,认为其未达到GMP标准。对桂林第一制药厂只进行了书面上的检查也认为未达到GMP标准,甚至从青蒿素生产青蒿酯所使用的设备和建筑来看它们都未必能符合GMP标准。
调查组对桂林第二制药厂的消毒,建筑的设计、结构和维护,蒸馏水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每个环节都指出了10余处的不符合规定的方面,比如消毒过滤设备装在不消毒的地方,沸水(100℃)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消毒方法等等。鉴于对昆明制药厂和桂林第二制药厂的状况持“缺乏GMP”的否定态度,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又临时要求请检查员到上海看看当时国内生产水平最高的上海信谊制药厂。结果,结论一样是不符合GMP要求,最终认为信谊制药厂也不适合生产用于中国以外的青蒿酯无菌注射剂 。
1982年9月29—30日,卫生部科技局局副局长周敏君主持了总结会,TDR依据此次检查得出结论:“均不符合生产青蒿琥酯静脉注射剂的条件,因此中方提供的青蒿琥酯制剂不能用于正式实验研究和提供国外临床试验”,“目前青蒿酯钠的生产不符合GMP标准,因而导致TDR所建议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项目还不能开始进行” ,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发青蒿酯钠在中国以外进行临床观察的研究计划时间要予以重新考虑。这一结论让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担忧其与TDR已达成的合作内容要全部推倒重来,甚至终止。因此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上报卫生部领导,请他们直接与WHO / TDR对话,寻找解决办法。特里格提出两条解决途径:第一是由中国自己建造一个符合GMP标准的新的车间或者改建一个新的车间,其二是由中国以外的合适的研究所生产一批符合GMP标准的青蒿酯钠,CHEMAL同意帮助中国在中国以外选定一个研究所。
在1981年10月后中方与TDR讨论的会议纪要中,一再强调了中国有关部门和CHEMAL只是在发展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抗疟药的科学领域内合作,而不涉及商业与生产活动。中方的原意是:与商业或者生产相关的活动将在中国进行或是由中国有关部门直接安排在国外进行。但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对包括GMP、样品供应、委托生产等,双方对上述原则则有不同理解,导致磨合困难。
考虑到维系与WHO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以青蒿酯钠一个药物为开发对象,而是中国开发的青蒿素衍生物系列药物走向世界需要得到WHO的帮助。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以“反复研究,权衡利弊,争取时间,尽快完成国际注册,保障我新药开发权益为上策”的策略,经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齐谋甲批准后,1982年11月16日(实际到达时间可能是12月),周敏君代表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回复特里格信函称:“计划在中国按GMP要求筹建车间,同时探索与国外适合的单位,如与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WRAIR)协作,加工一批量制剂和进行有关的,甚至全面的研究合作的可能性,希望你能协助联系合作单位并提出进行合作的具体建议,以便共同商讨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由此掀开了与美国国防部隔空谈判、以及在桂林和昆明建设国内GMP标准车间的序幕。
2. 与美国的谈判
1983年1月4日特里格博士回信周敏君:接1982年12月13日的信后已正式写信给WRAIR实验治疗部主任坎菲尔上校,请予合作,如经美国当局批准,应召开一次有中国、美国以及WHO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三方人员参加的会议,阐明合作细节,确保开发工作迅速落实。特里格还告知与中国合作的培训项目已经TDR特别规划处处长批准 。根据1984年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的《与WHO合作开发青蒿素备忘录》显示,在1983—1984年间双方信件往来相对频繁,主要内容有:“1月26日正在举行的WHO第71届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特里格与中国参会代表王连生约谈,并写了一个备忘录,请王连生带回 。备忘录中的主要内容是:
备忘录
WHO已同WRAIR联系,该研究所告之正式答复还有待美国有关当局决定,但生产一批青蒿酯的全部计划已经做好。建议三方于4月初在日内瓦或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考虑到中国方便在北京开更好。另外,据悉CHEMAL资助的李国桥将到曼谷Machidol大学,可能要带足量的青蒿酯钠在泰国进行临床前试验,这将有损于中国当局和CHEMAL利益,并为WHO所不赞同,因此请周敏君注意既不要李带青蒿酯去泰国,也不要让他在泰国进行任何青蒿素类衍生物的试验,并要求提出书面保证。
原本李国桥是应邀去泰国访问,拟带少量青蒿酯与甲氟喹作对照,后未被批准而放弃。鉴于李国桥准备带药到泰国进行试验的工作确实不是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与TDR批准的项目,因此卫生部科技局回特里格称:“无意让李带青蒿酯去泰国。”
实际上早在1979年,获英国惠康基金会(Welcome Trust)资助,在曼谷一所大学开展疟疾研究的科学家怀特(White)研究小组就开始与李国桥接触。1980—1981年间在香港进行甲氟喹研究的阿诺德(K. Arnold)与李国桥在国内进行了青蒿酯钠与甲氟喹的临床对比试验[11]。TDR阻拦李国桥带青蒿酯到泰国试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TDR自身的利益,阻止英国惠康基金会抢先。
2月10日,特里格博士致信周敏君,告知他将于2月14日访美与WRAIR讨论开展青蒿酯合作的可能性,需了解中国交付3—5公斤青蒿酯的最早时间。周敏君指示卫生部科技局回电:数量、时间中方无问题。3月11日特里格博士致信周敏君,告知已与WRAIR讨论,起草了计划并确定了制备方案,估计从收到青蒿酯原料后七个半月可完成制剂生产。为了缩短时间,希望中国同意在与美国的方案未批准前寄去50克药品让坎菲尔做试验。同时还说WHO总干事2月11日向华盛顿送交正式要求,使之能尽快得到批准合作。他还说到访美期间与霍宁(M. Horning)教授会晤后对青蒿素血药浓度含量测定学习班的计划进行了安排。

►1983年10月体液中含量测定方法学习班照片
供图:曾美怡
为此,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于1983年3月21日向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提交了青蒿酯国际合作谈判方案的请示报告 。报告介绍了合作的背景,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内容,特别强调只是技术合作不涉及商品经济利益;有关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生产工艺技术秘密和开发研究权等,联合国法律部应予保护;中方与美方的技术合作是通过WHO直接安排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由WHO做出保证,双方的合作仅限在青蒿酯的制剂加工和完成青蒿酯国际注册所必须的试验资料数据,最后达到国际注册的目的。1983年5月10日,特里格博士来电告知美国国防部国际卫生事务处主任布朗(Jerry M. Brown)中校、WRAIR的海佛尔将于5月31日—6月2日来中国谈判此事 。由于周敏君当时在外地开会,5月24日才回复特里格,希望美方能够将合作协议先寄来,经讨论后再确定会谈时间。

►1983年10月体液中含量测定方法学习班实际实验操作
供图:曾美怡
1983年11月1日,卫生部国际处并驻WHO代表陆如山转来特里格博士的信件和美国国防部的协议书草案(15条)。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将文本复制分送给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主要成员。11月20日,秘书处草拟了对“协议书的意见送交有关领导传阅,提到对协议草案中的5条内容有异议,中方认为更多的应该由中方人员参与其中的一些关键性工作,而不是由美方主导,在涉及合作的领域也主要是科研领域而不是商业利益”等意见。12月22日,秘书处收到特里格博士的信及协议书正式文本,信中说明这是WHO与WRAIR的意见文本,美国国防部已同意协议,并为协议书草案的起草用了6个月的时间致歉,并希望中方尽快就此安排三方会晤讨论细节。
协议书的内容包括三部分:
⑴ 制定协议书的根据;
⑵ 三方在协议中应承担的责任和权利;
⑶ 协议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处置。
12月23日,许文博召开会议,唐由之、佘德一、姜廷良、张逵、李泽琳、王秀峰、周克鼎等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对美方起草的协议书进行了讨论。秘书处首先汇报了对协议书的意见,认为协议条款是“主次颠倒,取而代之”,“条件苛刻,喧宾夺主”,“混淆发明,企图获利”,对WHO为中国科研人员培训和中国科研人员前往进修附加的条件也认为不够合理,不能够和协议书结合在一起 。1984年1月,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写信给卫生部外事局局长徐守仁,拟趁他前往日内瓦开会之际给TDR主任卢卡斯(A. O. Lucas)带去关于青蒿素与WHO合作的几点原则意见:
⑴关于对美国国防部起草的“青蒿酯合作研究协议书的意见”,提出一些条款是必要的,一些条款有待协商,一些条款尚须澄清,协议已报上级有待批准;
⑵完全同意卢卡斯博士关于新的1984年加速青蒿酯开发研究合作的建议;
⑶中国政府已批准在中国新建符合GMP青蒿酯生产车间;
⑷中国科学家愿意为人类的抗疟灭疟工作及其活动中积极做出自己的贡献,希望WHO利用自己的职权有效的保护中国在开发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活动中的正当权益;
⑸会谈的时间可以安排在1984年的3月或4月 。
1984年2月17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处就协议草案提出意见。同一天卢卡斯博士来电告知将于3月13日来华会谈与美国合作方案以及对修改协议书的意见。2月21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正式向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提交了关于合作开发青蒿酯谈判方案的请示报告 。2月27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主任许文博正式回复卢卡斯博士欢迎他来中国访问的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对协议书草案的意见:中国科学家愿意为WHO抗疟活动作出贡献,希望WHO利用自己的职权,保护中国开发青蒿酯的正当权益等 。3月2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准备好《情况分析与建议》报告供指导委员会讨论参考,1984年3月8日起草好送审稿《对“青蒿酯合作研究协议书”修改的建议》(中英文稿) 。
1984年3月14日,TDR主任卢卡斯博士、韦恩斯德费尔教授和P. I. 特里格博士与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就与美国合作的事务,在卫生部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就协议中的一些疑问进行了讨论,WHO也就一些协议条款进行解释,修改了协议条款。然后就具体的合作计划进行了商谈,包括研究提纲、研究内容、计划的实施,WHO与中国当局的联系,青蒿酯的商业性生产和WHO同意帮助中国了解有关青蒿酯制剂研究中可出现的相关专利等。5月3日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向国家科委和外交部提交了《关于提请批准〈合作研究青蒿酯协议书〉的报告》,([84]卫科教字第29号)。同年10月10日卫生部、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上报国务院《关于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共同开发抗疟药青蒿酯的请示》,([84]卫报科教字第52号)。此报告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国务委员姬鹏飞批准。11月5日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主任许文博致函卢卡斯博士,送达中方最终由国务院批准的协议草案文稿。然而,直到1985年3月13日,WHO总干事马勒才回复中国卫生部长信函 ,对中方的协议草案提出了修订意见,信函说WHO“愿意采用你们的草案,然而,对WHO和美国国防部已经同意的1983年10月的协议书作出的若干修改,这可能推迟美国官方的赞同,因为他们可能不会照办。”马勒还对协议书的许多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中国能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再提出建议,以便WHO能提出一份三方均能接受的协议书。因此,从1984年3月会谈开始到1985年3月整整一年的时间,由于三方均有各自的想法,对协议书的具体条款意见不一,不得不反复磋商,这里面有既有外交、政治方面的考量,也有诸多技术因素的影响。
1985年5月20日,中方以卫生部科教司的名义写成了复核意见 ,基本上同意了WHO的修订,但增加了“拟在条款中加上‘由中国科学家把药带到美国’,而不是WHO提出的把药交给美国国防部”的意见。卢卡斯博士于1985年8月21日与陆如山交谈并请他带了三个备忘录,首先他感谢中国带给他一公斤青蒿素,有利于加速抗疟药青蒿素系列衍生物的进一步研究,同时他提到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布罗西博士实验室近期进行的研究工作表明青蒿酯在某些条件下并不稳定,给今后的实际应用带来了困难;鉴于此CHEMAL建议1985年应进行更多的青蒿素类化合物和制剂的稳定性研究。CHEMAL考虑有几种衍生物,包括乙醚类化合物,布罗西博士已同意第一步先通过一个小的合成计划来确定看是否值得进一步研发的稳定衍生物,而且布罗西博士、CHEMAL已经和一名中国科学家在探索该领域的潜在合作。
在这一期间,中方提供的青蒿素送到一个符合GMP条件的实验室,开展了下列研究工作:1. 化合物的单独分析;2. 对目前的一些标准研究正在由CHEMAL进行,诸如从植物中提取和植物组织培养生产青蒿素方法的改进,合成适用于在动物模型上进行研究的放射标记化合物和合并用药的制剂。在肯定稳定衍生物或剂型之后,这批青蒿素按GMP标准制备成适当的化合物供进一步临床前研究,该项研究的详细计划在1985年10月14—16日召开的CHEMAL指导委员会上进行了讨论。这个备忘录可以看做是终止青蒿琥酯优先开发的一个预告,即发现青蒿酯不稳定,因此TDR决定放弃开发,也可以看做是TDR / CHEMAL决定结束青蒿琥酯开发转而与美国合作开发蒿乙醚(中国科学家在开发青蒿素衍生物的时候就已合成蒿乙醚,但因效价不如蒿甲醚而被淘汰)的理由。
1983年1月到1985年9月长达2年半,青蒿素指导委员会通过TDR与WRIAR的隔空谈判,始终未能坐在一起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各方在安排合作上的目的、做法和实施的可行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各方对权利和义务的争议不断,每次条款修订长达半年的时间。由于我国已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成果公开发表,此期间,国外在青蒿的引种栽培、育种和种植试验、药理研究,以及衍生物的研究均已全面启动。美国军方在美国本土也寻找到青蒿和提取出青蒿素,肯定青蒿素功效的文章于1985年在权威刊物《科学》(Science)上发表[12]。最终,TDR以青蒿琥酯不稳定为由放弃了与我国的合作研发。
从1982年到1985年TDR / CHEMAL决定支持美国开发蒿乙醚为止,青蒿素指导委员会与TDR / CHEMAL在青蒿素方面的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向中国提供了WHO出版的GLP和GMP规程文件。
资助了中国7名科技人员出国进行专业培训或技术考察。
提供8只Beagle种狗和部分仪器设备、试剂。
资助举办“建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生物体液中含量测定方法学习班”。
资助美国FDA国际调查部调查员到中国检查GMP。
参与卫生部与美国国防部就青蒿琥酯的生产合作的谈判。
接受中国提供的青蒿素样品(最多一次1公斤)。
这个历时几年的合作最后不了了之。在这段时间里,国外对青蒿素类药物的研究十分迅速,从1985年8月WHO出版的《简报》 上可以看出,TDR在未予中方通报的情况下,单方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展研究项目,包括从植物中提取青蒿素(1公斤数量)、改进从植物中提取生产青蒿素工艺技术、合成新的衍生物等六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公开招标。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对国际药品政策的不甚了解以及国内的各种条件所限等种种因素,中国错失了青蒿素类衍生物在国际上申请专利的最好时机,而当时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明早已经公开了。
这场合作失败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了国内“自力更生,以我为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在1984年提出的如下设想和对策 ,
⑴继续争取WHO“对中国有利的支持或资助,但不能等、靠、要,更不能让其捆着我们的手脚”。
⑵加紧国内工作,建设GMP车间,“这条开发药的路子迟早还得靠我们自己来走,国外援助总是暂时的,也代替不了我们的工作”。
⑶积极寻找其他渠道加工制剂,协助在国外进行国际注册的可能性,确保药品在国际上生产销售的权益。
⑷积极开展双边技术交流,打开通往疟疾流行地区、国家销售药物的渠道。
这些设想在随后的若干年间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得以实施,这也是当时中国青蒿素类药品拓展国际市场和合作所采取的步骤。虽然最初中国与WHO进行青蒿素类药物合作开发与生产的设想最终未能成功,但WHO对中国药物研发提供了诸多技术援助,为中国的药物生产规范向国际标准靠拢,建立自己的药物审批制度以及为后来与国外制药企业合作等积累了诸多经验。
经验与启示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在青蒿素研发过程中的突出贡献。然而,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研发历程中,在中国药品打入国际市场的竞争里,还有许多科研人员、医药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埋头耕耘、默默奉献。回顾我国青蒿类药物与国外合作的历史进程,诸多遗憾更是令人扼腕。不过,也可以从合作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教益。
1. 专利的缺失,合作优势缺失
在世界疟疾流行趋势严峻,急需新药取代已产生抗药性药物的形势下,我国成功地研发的新药,但却未能进入国际市场?青蒿素类药物至今无疑是中国药物研发对世界药物最大的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科研与管理人员缺乏药品发明的专利保护意识。在对外交流不畅的环境下,中国不仅没有自己国家的专利制度,对国际专利的认识更是无从谈起,由此导致在1976年为了防止成果被人抢先发表而急于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注册专利保护。或许当时认为能把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就非常不错了,抢在国外研究人员之前发表成果也成为科研人员为国争光的唯一选择。
中国当时没有专利制度,1981年10月,WHO在中国举办第四次疟疾化疗会议,中国科研人员在会上报告了青蒿素的分离和结构测定、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化学和化学研究、抗疟效价和作用机制的初步研究、药物代谢及药代动力学研究、急性亚急性及特殊毒性试验报告和临床适用报告等,基本上是将所有资料和盘托出。不过,即使在WHO会议上公开了一些研究数据,只要会前申明了保密的话,中国的青蒿素类药物与WHO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优势的。由于药物没有专利保护,在与WHO商谈合作时,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掘金的基础。
2. 药品生产规范、管理制度的缺失
1980年代初,由于国内政策制度尚不健全、经济发展和技术设施还比较落后,导致青蒿素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步履艰难。TDR / CHEMAL提出的合作开发青蒿琥酯注射剂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厂家要符合FDA现行GMP的标准,而我国的生产厂尚未建立这样的管理规范。由于当时我国在药物研究、生产等规范上的制度缺失,使得技术合作中的诸多事宜无法谈拢,合作双方相互猜疑,致使合作难以继续。
我国药品管理制度改革逐渐向世界先进管理模式靠拢,但时至今日,国内法规与国际法规的管理和规范还有很大差距,从而造成了仅有国际新药发明权,而没有国际上各国药品注册销售权的被动局面[13]。
3. 从中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青蒿素类抗疟药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药物史上里程碑式的贡献。但如何突破市场壁垒,走向国际,在改革开放之处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此后,我国借助国际医药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完成了该药品国际上市前最关键和最耗资的临床试验研究,得到了按国际规范标准临床试验的预期结果。借船出洋,加快了中国研究机构和医药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在吸取了与TDR / CHEMAL合作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国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药物的国际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青蒿素成为中国医药界贡献给人类健康的标牌。
参考文献
[1]李国桥等. 青蒿素类抗疟药[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2]黎润红. 523任务: 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现[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1. 32(4): 488—500.
[3]黎润红等. 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3. 35(1): 107—122.
[4]黎润红. 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5.
[5]饶毅等. 辛酸与荣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谢华宴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坎道博士等[N]. 人民日报第五版. 1972-08-06.
[7]张炜逊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技术合作备忘录签字[N]. 人民日报第六版. 1978-10-06.
[8]陈慕华副总理会见马勒博士 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技术合作备忘录签字[N]. 人民日报第四版. 1978-10-06.
[9]周廷冲等. 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讨论会[J]. 药学学报. 1982. 17(2): 158—159.
[10]张逵. 再忆周克鼎.青蒿情.黄花香[M]. 蓝天出版社. 2008. 47-52
[11] Li GQ. et al. Randomi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mefloquine, qinghaosu and pyrimethamine-Sulfadoxine in patients with falciparum malaria[J]. LANCET. 1984. 2(8416): 1360—1361.
[12] Klayman, Daniel L. Qinghaosu (artemisinin): An Antimalarial Drug from China[J]. Science. 1985. 228(4703): 1049—1055.
[13]刘天伟等. 复方蒿甲醚国际合作的回顾与思考[J]. 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 2004. (4): 44—53.

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14卷2期,有删减。主要内容收录在《继承与创新-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一书中,也是纪念中国五二三任务开展50周年系列文章之一。
制版编辑:核桃林丨